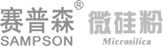鐵礦石資源稅改的攔路虎
自2002年起,鐵礦石資源業內就有調整資源稅標準的要求,但是其中困難頗多,想開展調整還需要解決多項問題。
第一點是如何實現鐵礦山企業減輕稅收負擔。
現在,我國對鐵礦山征收的稅費除了一般工業企業的增值稅、所得稅等外,還征收從量定額的資源稅、從價定率的礦山資源補償費、探礦權使用費、采礦權使用費及地方政府征收的合計25種以上各種稅、費、基金。目前,鐵礦山企業總體的稅費負擔率達到25%以上,主要原因是圍繞著鐵礦山資源有償使用而征收的稅負過重。
實行鐵礦石資源稅改革,能改變資源稅征收標準不隨鐵礦山開采條件變化而調整的現狀,但國家財稅政策的首要功能仍然是為國家組織財稅收入,稅改前后國家的稅收不可能大幅下降,通過鐵礦石資源稅改革實現鐵礦山企業減輕稅收負擔存在一定的難度。因此,鐵礦石資源稅改革應制定具有可行性的方案,并選擇適當時機進行。
第二點是“清費立稅”的效果預期可能影響改革進度。
資源稅改革很難,其中很大一個原因是理順礦業領域各種各樣的收費。資源稅改革的政策指向十分明朗,就是要進一步推進“清費立稅”,理順資源稅費關系。鐵礦山資源是地方稅收的一個重點,部分地方政府過度征收,導致礦山企業負擔過重。清理收費的效果決定著鐵礦石資源稅改革的成敗和鐵礦山企業的存亡,從稀土、鎢、鉬資源稅的改革情況來分析,可通過資源稅改革,提高資源稅標準,吸納資源補償費,將資源補償費降為零,停止征收相關價格調節基金。
然而,由于“清費立稅”觸及了部分部門和地方的既得利益,如果新的收費項目出現,可能會導致企業實際負擔大于稅改以前,導致資源稅改出現相反的效果。因此,規范收費行為是鐵礦石資源稅改革所要面臨的首要問題之一。
第三點是如何約束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權。
根據國家對資源稅改革的要求,鐵礦石資源稅改革必然是和稅費改革同步進行的,關鍵在于稅改的執行力須兼顧各方利益的平衡。從已進行資源稅改革的資源種類來分析,資源稅帶來的收益增長大概與取消收費的損失相當,但為確保財政收入,地方政府部門在稅率制定上很可能盯上高稅率,比如煤炭資源稅稅率幅度定為2%~10%,具體適用稅率由省級財稅部門擬定。如果地方政府持續實行高稅率,那么既不能體現資源稅改革的優越性,還會傷及鋼鐵行業的利益,對中央決策威信也是個挑戰。
第四點是如何體現鐵礦資源稟賦的差異。
目前,為體現鐵礦資源條件,鐵礦石資源稅將所有鐵礦山進行評估劃分等級,從量計征,按開采多少礦來交資源稅,造成了開采企業“嫌貧愛富”,富礦被亂采濫挖,資源利用很不合理。改為從價計征,資源價格隨行就市,價高則多納資源稅,價低則少納資源稅,使得資源稅由增加財政收入、調節資源級差收入的一般稅,轉為運用稅收杠桿的調節作用,為國家經濟政策目標服務而設立的特殊稅種,有利于鐵礦山行業節約資源、保護環境。
但如果稅率無法明確區別應用,缺陷也由此而產生。一是難以體現資源本身價值,資源稅的本質特性是級差地租,從價計征與之相距較遠,征多少資源稅要體現資源本身的價值而并非資源產品的價值。資源條件最差的鐵礦石與資源條件最好的鐵礦石采選出來的鐵精礦的市場價值沒有明顯區別,然而它們的采礦成本卻可以相差數倍,進而導致盈利水平大不相同,說明了資源本身的價值是不同的。二是對不同稟賦條件的鐵礦石資源征稅相同或相近,有失公平。資源稅具有級差地租的性質,即對交通便利、賦存條件好、品位高、易采易選的優質資源多征稅;對交通偏僻、賦存條件差、品位低、難采難選的劣質資源少征稅,以此減少因資源優劣差異而導致的開發企業苦樂不均,促進采礦權人公平競爭,從而使礦產資源的開發達到合理有效。近期,國家財稅部門已經意識到資源稅從價計征的問題,在實施稀土、鎢、鉬資源稅清費立稅、從價計征改革中,關于適用稅率已經明確:輕稀土按地區執行不同的適用稅率,其中,內蒙古為11.5%、四川為9.5%、山東為7.5%,中重稀土資源稅適用稅率為27%,實際上設置了4檔稅率。這表明,“資源稅應體現資源優劣”的原則已被國家相關部門所接受。